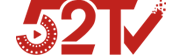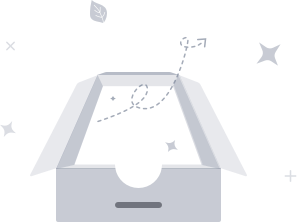一部适合高敏感人群的电影?专访《阳光照耀在青春里》导演
今年的“清明档”呈现出了一个趋势,三部电影都集中聚焦了边缘群体:张艺兴在《不说话的爱》中扮演听障人士,赵丽颖在《向阳·花》扮演出狱“更生人士”,肖央在《阳光照耀青春里》扮演精神障碍者。三部影片选取的现实题材,都让它们颇具社会意义。
其中《阳光照耀青春里》是较为特别的一部。尽管本片在票房表现上不佳(目前仅有500多万),但被不少小众影迷视为“清明档”的遗珠,甚至被部分观众称为中国版的《飞越疯人院》。

导演曾海若。
《阳光照耀青春里》的诞生源于导演曾海若长达七年的剧本打磨与医院实地调研,每一帧意象都浸染着真实病例的肌理;它拒绝类型化的爽感叙事,转而以跳跃的节奏与繁复的隐喻,模拟被困在情绪孤岛中的心灵图景。
面对两极分化的口碑,曾海若对南都记者坦言本片确实是一部有些许门槛的电影,而票房困境似乎也印证了电影的主题——当短视频时代不断压缩观众的耐心,是否还有人愿意凝视那些被社会定义为"不正常"的孤独灵魂?

01
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
南都娱乐:你曾经在新闻中心当过编导,又拍摄过不少纪录片,都是侧重于记录现实的,而你的首部剧情片则是拍摄精神病人天马行空的世界,为何选择这一题材?过往的工作经验对你首部作品有何帮助?
曾海若:我在新闻中心当了五六年编导,那时就发现身边很多做电视的人都有抑郁症、焦虑症。当时"抑郁症"还算新鲜词,后来逐渐出现躁狂、躁郁等各种精神问题,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,我也有好友深受其苦。最初是一种很现实的感受——我发现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,竟然在中学就开始出现各种精神、心理问题。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社会话题,我一直想涉及这个题材。
2015到2017年间,经常看到关于"被精神病"的报道。当时讨论很多,比如被老板送进医院维权,或争家产被妻子送进去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颁布后,影响了一批人。由于曾经的工作经历,我一直关注这类题材。从纪录片创作经验来看,最大的帮助在于事实调研方面。做纪录片习惯挖掘真实,电影里几乎每个人物都有我调研过的现实人物的影子,也参考了很多当时的报道。
南都娱乐:影片中那个叫“青春里”的精神病院是个“圆形监狱”的建筑结构,醒目的视觉符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家福柯的《规训与惩罚》和《疯癫与文明》,你个人是否受到过他的影响?

法国哲学家福柯。
曾海若:没到那种程度。具体来说,“圆形”更像是精神病人的日常行走模式。不论是长形还是圆形楼道,患者都没有真正目的地,只是被困在往返路线上。关键还是我们主题中关于时间的设定——圆形建筑在片中类似钟表,每个绕行的人都是指针。这种循环意象其实源于实地调研:我走访多家医院发现,休息时间总有大量病人在楼道、操场等环形空间反复行走。这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他们总是匆忙走向某个点再折返,因此,我们设计了圆形建筑。这种结构营造出循环往复的时间感,仿佛行走既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。
南都娱乐:为什么把一家精神病院改名为“青春里”?
曾海若:每次从医院调研出来时,我总会产生这样的想法——这里更像特殊教育学校。这里的人既不需要谋生,也没有社会职务。无论是局长、小贩还是农民,进入医院后都只剩下最基础的身份。与普通医院不同之处在于,普通医院的病人痊愈后就会离开,生病期间仍保有社会身份;但精神病院会完全剥离社会身份,你只是某个病症的患者,这让我联想到学生或孩童。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充满童真特质:相对天真坦诚,擅长幻想,被困在独立的时间维度中。即便面对一小片荒地,他们也能想象成草原或化身动物。因此,我决定用"青春"来命名这所医院——这个既承载年龄特征又具有时间感知的名字。

南都娱乐:除了“圆形监狱”,影片中还有小矮人、森林、树木、钟表等意象,每个意象都有明确的所指,你在构建这套象征系统时,是否担心模拟出来的精神病人视角太过理性了,反而出现失真?
曾海若:首先,关于作品的核心表达,我们在选择拍摄对象时就有所考量。影片并非旨在全面呈现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,而是聚焦于那些具备相对清醒意识却难以融入社会、因而长期住院的患者群体。
片中出现的小矮人、森林、钟表等意象主要源自真实病例及个人观察。例如树木意象,源于某位自认是树的患者,他会长时间保持站立姿态;外星人元素则来自将外星生物视为挚友的病例。关于钟表的概念,源于患者对时间的感知与外界存在显著差异。我希望展现个体如何被情绪困境——不论是思念、仇恨或愤怒——所禁锢,这些情绪困局本身也构成了独特的时间概念,正如医院环境对患者的时间禁锢。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。
02
这部电影确实考验了观众注意力
南都娱乐:影片中探讨了“正常与不正常”的边界,你眼中“正常”和“不正常”的区别是什么?
曾海若:正常和不正常其实有很多层意思。首先,正常意味着遵守社会公约与规则,尊重普遍共识。简言之,顺应共识即被视作正常,反之则被归为异常。但从精神医学角度看,自知力是关键差异点。例如常人在决策时虽会陷入多重心声的纠结,却能清醒认知这些声音皆源自自我意识;而精神障碍者真会觉得是别人在跟自己说话,甚至觉得有外星人操控自己。

再比如,诗人看到一棵树,会想象自己成为树,感受阳光,从而写出诗意的语言;而不正常的人会真的认为自己是一棵树,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。因此,越接近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,人显得越感性;越远离界限,则显得越疯狂。自知力的界限大致如此。
从更宽泛的角度看,生活幸福最重要。如果你的体验美好且幸福,这就是正常;如果过得痛苦,自我施压、焦虑,浪费了美好生活的机会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就是不正常。
南都娱乐:男主角何立为(肖央 饰)起初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,但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时,他意识到自己有病,甚至积极配合治疗。不正常的人意识到自己不正常,那他算正常了吗?

曾海若:对,当他开始有一定认知时,至少跨出了很大一步。但他并不够稳定,何立为当时也是受巨大刺激后,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,这本质上是应激反应。在精神分裂中,他从强烈的自我肯定变为强烈的自我否定,那一刻他处于巨大的自我否定中。虽然接受了,但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强烈否定,所以状态仍不稳定。并非察觉到就结束了,因为可能过度判断或否定自己,这也很不好。他需要药物和医院治疗来稳定。当他能清醒认识到幻觉只是脑中的声音时就可以了。
南都娱乐:我留意到电影里有着多次视角的切换,是否担心视角的不统一,会提高观众的观影门槛?
曾海若:创作和拍摄时没有强烈感觉,但现在的票房体现出观看门槛。如果要降低门槛,只需简单聚焦合理维权,表现维权困难直至成功。这是标准类型片写法,但我们不满足。我们不完全想表达维权,而是想更多表现精神病人作为人的权利。主角在精神病院遇到许多病人,他们互相治愈,这些病人也代表着主体。拍摄中我们确实关注到许多病例,可能显得线索过多,但本质上这些精神病人视角可视为对何立为的补充——比如洪兆庆(陈明昊 饰),他代表何立为的反面。所谓反面并非对立,而是何立为可能成为的另一种状态:拒绝沟通,为自我保护而封闭。何立为则主张打破界限,争取权利,即使身处困境也要活得有尊严。洪兆庆的线索本身也是在阐释何立为。只是两小时的电影容纳这么多元素,确实考验观众注意力。

03
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
南都娱乐:很多观众认为本片是中国版的《飞越疯人院》,你怎么评价?
曾海若:这是个误解。首先,这部影片远没有《飞越疯人院》伟大,几乎没有可比性,《飞越疯人院》是真正的高峰。其次,《飞越疯人院》的主题是个体与体制的对抗,而我们的主题是人内心的成长,以及争取权利的重要性——说白了就是"不放弃"。虽然某些情节相似,但这是题材决定的。

南都娱乐:有部分观众批评这部电影的节奏很混乱,还有叙事上很跳跃和细碎,这是否也是在模拟精神病人的视角?
曾海若:这是个很好的哲学解释。创作者确实模拟了精神病人的状态,整部电影都像处在精神病状态中。但我不觉得影片杂乱跳跃,它始终围绕我想表达的主题。不过这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,需要专注体会其中的联系,而不是直接降低观看难度、把各条线连起来,可能需要思考拼凑。很多观众二刷时会发现,答案和暗示其实都在前面,只是第一次看不容易发现。这确实影响了票房,相当于拒绝了很多观众。但从另一方面看,喜欢的人会觉得过瘾。
南都娱乐:影片中有一段《心恋》的舞蹈戏,这首歌也是电影推广曲,为何选择它?
曾海若:这首歌不是我选的。拍摄时大家觉得中秋节除了爆米花,应该有个狂欢的过渡段落。肖央提议跳舞,于是7号病室的演员们开始排练,那是个纯即兴的段落。
选择《心恋》是因为:第一,它很符合复古怀旧的影片调性,这些角色都是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人,对这首歌熟悉很正常;第二,这首歌本身有特殊含义,影片前半段每个人都显得孤立,后来才相互联系。所以,这首歌更多是集体创作的结果。
南都娱乐:这部电影故事的时间跨度有14年,但角色形象变化不大,是否象征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?
曾海若:没错,你看得很准,这也是我们讨论过的。其实很少有观众注意到这一点——离开精神病院的人老得快,比如方宁(国义骞 饰)搬出去前后差别很大。而在医院里,大家老得慢,时间流逝很缓慢,有点像在另一个星球。当然,这只是寓言式的表达,观众一般不会太注意人物容貌的变化。虽然有变化,但确实不大,在我的设定里,这些角色的变化就是很小。

何立为离开医院时,其他人还在医院里,这也是一种寓言——他们只是头发白了点,而这14年恰恰是他们相对年轻的阶段。
04
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偏向于高敏感人群
南都娱乐:这部电影的评价两极分化挺严重的。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似乎都代入到某些具体处境,从而产生移情。你觉得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画像是怎样的?
曾海若:当然,电影不应该拒绝任何人,谁都有权利看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,应该都有一定的影视鉴赏基础,喜欢看电影,也喜欢独立思考,不会简单否定事物,对问题和自己看到的东西持敞开的态度。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对生活总体很敏感,这种敏感自然也包括心理上可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问题,可能遭受过情感、工作或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挫折,所以他们对电影表现的东西会有同感。但这并不是说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就没有这些特点。这是个很神秘的研究领域。但总体来说,我接触到的喜欢这部影片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。他们不会因为电影不取悦你、不符合便利的观看需求就生气。
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,尤其是做商业类型片的人,都在拼命想观众喜欢什么,但观众类型实在太多。可以肯定的是,观众会越来越不接受挑战自己观影体验的东西。可能是短视频越来越多,大家的耐心变少了,会觉得花费两个多小时看一个不那么舒服、不怎么得劲、跟自己观影习惯不一致的东西,就会排斥。
南都娱乐:那在路演期间,观众给到你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?
曾海若:路演时很多反馈让我既感动又意外。来看路演的人本身就对影片有好感,很多人观看时都代入其中。我有个20多年没见的律师朋友,专程从重庆赶来看。当时我很忐忑,因为他接触过很多社会阴暗面和悲惨人生,自己也被这些事困扰。但他说非常感动,还写了长篇评论。这样的观众很多,比如有大学生看后当场痛哭,因为他们也深陷心理困境——这不是爽片能表现的。爽片只告诉你摆脱困境有多痛快,而这部电影是和观众一起面对痛苦,重现那些难受的回忆,体验感很强。排斥这种体验的观众可能不容易看懂。在和观众交流时,我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代入感。这种沉浸式的共情,正是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。
南都娱乐: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,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偏向于高敏感人群(HSP)对吧?这一代人普遍都对很多事情很敏感,这种敏感的特质是时代的进步,还是一种退步?
曾海若:是的,他们总体比较敏感,但这只是时代的特点。我不知道对时代而言是进步还是退步,但对人来说,这至少是自身的进步——更尊重自己,更关心内心感受,而不是忍受或麻木。敏感让他们懂得宣泄,对苦难、孤独甚至他人更开放,不会因自闭症或强迫症视人为怪胎。从这个角度说,这绝对是进步,但我不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。因为生活中影响太多,我们必须内心强大,在敏感的同时保护自己,坚强地接受阳光。这也是电影的主题。
作为导演,这部电影现在也处于类似状态,快被现实市场打懵了。想做不同的东西,但市场宽容度很低。其实不只电影市场,各行各业、日常关系中,想表达不同都很难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践行主题:把困境当作机会和养料,相信永远有阳光,这些养料会助你成长。即使票房不好,我们也有机会讲出困惑,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电影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好事。
南都娱乐:本片的小众题材确实影响了票房表现,如果给你机会重拍,会不会为了市场做出妥协?
曾海若:我做这部影片时并不觉得是小众题材,因为影片不是纯粹拍精神病人,而是拍被内心和外围困住的人,其中包括精神病人。如果重拍,我可能会想如何更简洁地表达主题,肯定会调整。但这部电影是七年前写的剧本,这些年我有了更多生活体验,电影本身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。如果能以现在的状态重写,肯定和年轻时不同,能更好地平衡表达与呈现,让它更易理解。我相信随着技术和技巧的成熟,再拍肯定会不一样。